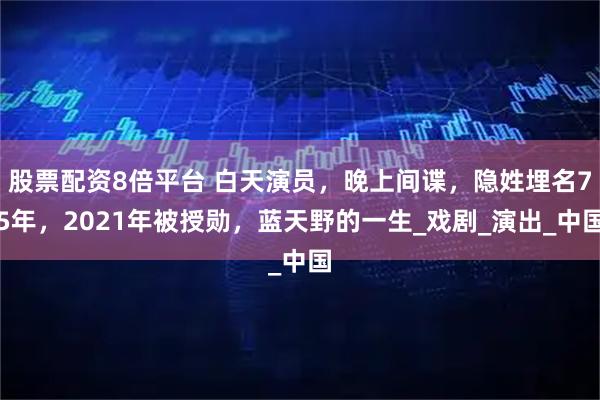
94岁的蓝天野在轮椅上接过“七一勋章”时,人民大会堂内的掌声淹没了轮椅的声响。银幕上那个仙风道骨的“姜子牙”股票配资8倍平台,此刻胸前的勋章光辉,映照出一段令人震撼的历史——这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,还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:北平解放前夕,穿梭在生死边缘的地下情报员。
他用75年时间隐姓埋名,从秘密交通员到戏剧巨匠,人生轨迹犹如他塑造的经典角色一样,充满跌宕起伏的戏剧性。
一个学油画的文艺青年,如何变成了地下尖兵?一个改过名字的演员,为什么能演绎出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?到了94岁高龄时,他又凭什么成为戏剧界唯一的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?
出生于河北饶阳县的王润森,从未预料到自己会与“蓝天野”这个名字结下深厚的缘分。1944年,17岁的他考入国立北平艺专油画系,怀抱着画家梦,站在画架前,憧憬着未来。然而,历史的浪潮在此刻改变了他的命运——来自解放区的三姐石梅将新家转变为中共地下联络站,忙碌地印刷传单、传递情报、护送人员,革命工作昼夜不停。
展开剩余81%1945年9月23日,18岁的王润森在姐姐的引领下,秘密加入了党组织,这个日子他永远铭刻在心:“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。”
北平的剧场成了他的战场。19岁时,他居然穿上了国民党少校军装作掩护,开始在演剧二队和祖国剧团中积极发展进步力量。1948年秋,北平笼罩在白色恐怖中,作为地下党员的他被命令前往解放区。在途中,组织要求他临时改名,他脱口而出“蓝天野”——一个完全不曾预料却要伴随他一生的名字。那时,他并不知晓,这个随意改变的名字,未来将响彻中国戏剧界。
身份的切换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:白天排演启发民众的进步戏剧,深夜则默默传递机密文件;台上演绎角色,台下过着另一种身份的生活。
开国大典前夜,22岁的蓝天野站在金水桥前,目睹解放军进城的壮丽场面。他在回忆中写道:“官兵全副武装,最显眼的是大皮军帽,都是辽沈战役的战利品……北平全城沸腾,老百姓欢欣鼓舞。”军帽上的弹痕依旧,而他已经准备好用艺术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。
1952年6月12日,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成立,25岁的蓝天野作为建院元老迎来了全新的舞台。首任院长曹禺提出了将剧院打造成“莫斯科艺术剧院水准的话剧院”的远大目标,点燃了年轻演员们的雄心壮志。
从地下尖兵到舞台艺术家,他用三十年的时间,塑造了半部中国话剧史。
《茶馆》的排演现场,成了蓝天野的“社会大学”。为了演好民族资本家秦仲义,他专心研究前门大栅栏的商人风貌;揣摩老北京茶客的神态时,甚至反复推敲群众演员手中茶杯的摆放角度。从1957年首演到1992年告别舞台,他共演出了374场,从风华正茂的青年,演到鬓发如霜的老者。
特别是最后一幕,三个老人相互诉说沧桑的戏,导演焦菊隐排练整整一夜,最终引导演员们找到了那种从心底发出的倾诉感。
1992年《茶馆》告别演出时,观众久久不愿离去,在首都剧场外默默守候。蓝天野推着自行车,总会特意下车,在夜色中与观众握手告别:“演员必须用真诚的敬意回报观众。”
1980年,《茶馆》赴欧洲演出,中国话剧首次走向国际。德国媒体用“东方奇迹”来形容这场演出,更有人感叹:“看了《茶馆》,我才明白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。”当西方观众通过艺术理解中国革命的深层逻辑时,蓝天野在后台默默流下热泪。
1992年《茶馆》封箱后,蓝天野似乎要正式“封神”——在电视剧《封神榜》中,他塑造的姜子牙角色深刻入木,仙风道骨,至今无可超越。
在书画上,他也找到了新的寄托。毕业于北平艺专的他重新拿起画笔,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,家乡衡水书画院更特地邀请他担任名誉院长。但没有人预料到,七十岁后他竟开启了艺术生涯最辉煌的“加时赛”。
2011年春,北京人艺食堂里的一场“鸿门宴”,让蓝天野的轨迹发生了转变。84岁的他应邀复出演出《家》,这已经是他19年来首次登台。排练时发生了意外,他不慎摔伤了手指骨折,但他依旧说:“对不起大家”,第二天仍坚持带伤排练。
这一次,他主动挑战了反派冯乐山,舍弃了自己一生所扮演的正面形象。当大幕拉开,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垂暮老者,而是一位艺术生命正在逆生长的奇迹。
90岁后的蓝天野更成了舞台的“逆行者”:87岁执导《吴王金戈越王剑》,88岁排演《贵妇还乡》,93岁再次出演《家》中的冯乐山。2020年,他完成了一场演出后,缓缓走向后台,成为中国话剧史上最高龄的舞台表演者。
2021年3月,94岁的蓝天野仍在为《吴王金戈越王剑》复排工作。6月29日,面对“七一勋章”挂在胸前的那一刻,授勋词深刻总结了他一生的贡献:“将一生奉献给人民文艺事业。”
这位九旬的老人并没有停下脚步——他计划为北京人艺新落成的国际戏剧中心导新戏,作为建党百年的献礼。与此同时,他几十年来持续捐款支持社会公益:汶川地震捐款、义卖画作救助唇腭裂儿童、资助困境中的戏剧节等。
正如他常对年轻演员们的叮嘱:“德艺双馨,德永远在第一位。”
2022年6月8日,95岁的蓝天野安详辞世。回望他的足迹:从饶阳少年到地下尖兵,从人艺台柱到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,每个身份的转变背后,都蕴藏着“党的需要就是我的使命”的坚定信念。
94岁时,记者问他关于改名的事,他淡然道:“我这一辈子听党的话,党让我做什么,我就做什么。”
今天,北京人艺排练厅的墙上,依然悬挂着他最后的叮嘱:“演员拼到最后,靠的是文化修养。”这句话,或许就是他跨越两个世纪艺术人生的最简朴注解。
发布于:山东省启灯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